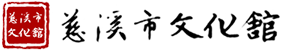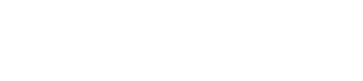张建斌
一
这是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的1960年代。
盛夏,草木葳蕤,蝉鸣啁啁,远山含黛,绿水东流。
龙门浦,慈北平原通向杭州湾的一条大河。每日午后,总有一群孩童相约在河里嬉戏,赤日骄阳下,绿水悠悠,鱼虾逐浪,四溅的水花形成一道道眩目的彩虹,河底水草碧油滑亮,如慈母的手,婆娑着孩子们瘦骨嶙峋的身躯。河旁,站着三两位纠结的阿妈。“水生,快上岸来,不要到河中央去”“阿凯,回家帮忙割麦”……这个叫水生的孩子最调皮,不但越游越远,还一个劲猛扎漩涡,捞起一根根水草和一枚枚贝壳,扔向玩伴,浑然不顾岸边母亲般的呼喊。
这条蜿蜒流经数个村庄的河,把一座山硬生生劈成了两半,两岸巉岩突兀,庋藏着流传千百年的不老传说。传说蚩尤被黄帝战败,化作一条蛟龙向沿海方向逃窜,慌不择路将眼前的大山撞成了两截,河就是蚩尤逃命时所留,龙门浦的名字就这样流传开来。山上的两个石抽屉,还藏匿了黄帝战蚩尤的兵器。
这河看似表面平静,但河床暗流汹涌,每遇台风、暴雨等极端气候更是喜怒无常,暴殄天物,周身散发着蚩尤的野性。三年前的一场春季暴雨,就把沿河的数百亩油菜地变成泽国汪洋。传说河里还有一头力大无穷的水獭,趁着夜色专门把河埠头的人拉入水,最近一次是半年前一个芦苇摇曳的深秋午后,生产队在龙门浦筑坝造闸,收工时发现少了一名队员,两日后在龙门浦的河埠头被发现,泡胀的肚子肥大,像喝饱了人血的花蚊子,手指都少了两根,大家事后说是被龙门浦里的大水獭啃掉了。
那名消失的队员,就是水生他爹。
水生,今年八岁,在大旱那年出生,父母干脆起名水生。水生家三代傍水而居,从小就在龙门浦泡大。自从父亲出事后,阿妈管教得更紧,往日里视为家常便饭的河边嬉戏,都有阿妈形影不离的尾随,像水里游泳这样的大事,阿妈自然是目不转睛盯着,生怕波光粼粼的河面突然出现一道口子,活生生吞噬了水生。水生有时不习惯阿妈的唠叨,更欺她缠过足走的慢,一溜烟和玩伴消失在家旁的橘子林中,阿妈飞快轮动小脚,要赶上这群顽皮的稚童已颇觉不易,有时便先到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蹲点,用慈母的眼神注视着孩子的一举一动。
“不好,有人落水”,不知谁家的孩子一阵乱喊,一个身影顺着河里漩涡渐渐下沉。这群七八岁的孩子,被眼前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懵了,他们平日在河里嬉戏泼水尚可,如何营救落水者,是一门从未触及的新学问,此时有跑上岸的、有愣在水里的、也有望着河面挣扎的手不知所措的,嚎哭、咒骂、尖叫声搅成一团。岸边的阿妈们心急火燎,却也都不识水性,眼见水泡一个个往上冒,只能扯足了嗓门往山那头的田野方向喊,男人们都钻在麦浪中劳作,又怎能听到?危急关头,水生阿妈不知从哪找来了一根竹篙,踮着小脚向河畔的水生伸,“水生,抓住竿子,靠近她”。水生一把抓过竿头,用他惯有的姿势扎进漩涡,吸一口气又钻入漩涡,岸上的空气如凝固了一般,阿妈和孩子们个个张大了嘴盯着看,水生妈口中诵着经文祝祷,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“抓到了,他抓到了”,其中一个孩子眼尖,瞅到水生顺着竿子从河面浮出,另一只手死攥住落水女孩的手不放。水生阿妈于是把竿子头交给了另一个大人,自己鞋也不脱,一个跨步入水,顺着竹竿朝河中央奔袭。幸好龙门浦河床是由数百年风侵日蚀形成的鹅卵石铺就,河底淤泥不多,夏季水又不甚深,刚漫过阿妈的肩头,母子俩合力硬生生将口鼻全是水草的女孩拖上了岸。
这名落水被救起的女孩,叫初春,小水生三岁,家住村头龙门浦东岸,离水生家五里路。
一周后,乡里送来一面“见义勇为”锦旗,奖给水生家所在的生产队,生产队开会表彰了水生母子俩,还送来两篮子鸡蛋。水生阿妈把鸡蛋用龙门浦水煮熟了,挨家挨户分给村里人,连初春家都分到了。
二
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。
龙门浦的1980年代,水波清漾。初春傍晚,两岸青山隐隐,桃林灼灼,晚霞打破阴翳,给山边的油菜田披上了一层镀金的外衣,垂髫童稚在田间追逐嬉戏,渔翁载着饱食的鸬鹚归来,对着潋滟水光引吭高歌:
“绿油油的江水哟,头枕夕阳,
一头挑着南,一头载着北;
我对你的爱恋哟,比那远山重,
恰似这,
孤独的炊烟,盼着夜归人。”
春水初生,落日余晖里,一对青年男女正沿着河畔的泥路漫步。
“水生哥,你还是去上大专吧,你学的机电挺实用的,学了数理化、走遍天下都不怕,这个年代更需要像你这样靠技艺吃饭的人。”说话的姑娘正当妙龄,扎着两根马尾辫,身形婀娜,肤白胜雪,两只大眼睛犹如一汪碧水,蕴含着无限生机与灵动。
“不,初春,这些天我想了很久,比起这里,我还是不太习惯大城市的喧嚣,在这个小村庄当老师挺好的,连空气中都有一股泥土的芬芳。还有这河,这堤坝,就是伴随我一路成长的朋友,这里的一切都已深深积淀在肌肤里,融入血脉中……”此时的水生,已出落长成一个浓眉大眼的俊朗青年。
脚下的龙门浦大闸,正张着大口,吐纳着来自大海的味道,腥咸的海风拂过水面,不时泛起一道道皴纹。坝旁的河岸矗立着一排“凹字型”金色琉璃瓦平房,院前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,这是全村最体面的建筑——水生支教的村办小学。这道土坝,如一条矫龙横亘于三十米宽的河面之上,河水通过坝闸,与近海丰枯调剂,让龙门浦收敛了原来的暴虐习性,成为沿河三十里农田旱涝保收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此时,水生用深情的目光凝视着大坝,脑海中盘旋的是父亲模糊而高大的身影,黄昏时分,父亲出海回来,端过一脸盆跳跳鱼和泥螺供水生赏玩,跳跳鱼蹦过一米多高,水花飞溅父子俩一脸……
“水生哥,在想什么呢,还得感谢你当年在这河里捞起了我,不然都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”,不知何时,初春红着脸嗫嚅,打断了水生的沉思,一双削葱手不自觉地挽住了水生结实的臂膀。四目相对,夕阳倏忽更加柔情无限。
水生噗哧一声笑了:“我还梦到过,不是我和我娘救的,是你自己赤着脚爬上了岸”。“你少胡说”,初春的笑靥红成了二月花,暮色渐浓,这对拉长的身影跨过土坝,迎着血红的夕阳继续行进。
三个月后,在乡亲们的见证下,水生和初春拜堂成亲了。
新婚夜,是一个大雨倾盆的台风夜。狂风挟带着暴雨,一阵紧似一阵呼啸而过,龙门浦一改往日的温良平和,浊浪如同万千奔腾的骏马,不断冲刷着河岸,整个大地在风雨中震颤——事后人们回忆,大概男主角叫水生的缘故罢,大喜的日子终于引来了无尽的水,一道来庆贺这段姻缘——屋外是风雨肆虐,水生家简陋的厅堂内,齐整整摆着四桌酒宴,水生妈笑得一天没合过拢嘴,水生和初春正不断给冒雨来道喜的亲朋好友把盏斟酒。房椽上的瓦片撞击声令人心悸,并不时有瓦片被风吹落在地,摔成齑粉,发出一阵阵清亮的怪啸。
终于送走了最后几位客人,忽然亮敞的屋内一片漆黑,“停电了”水生阿妈发出一声既感不安、又略带责备的叹息。是啊,弥足珍贵的儿子大喜日子,却有台风、暴雨和黑暗来凑热闹,看来今天确是一个谁也不愿错过的好日子。这时,水生似乎想到了什么,猛然从燕尔新婚的喜悦中回过神来,“阿妈、初春,看来今晚风雨还要大,我得去看看学校有没有漏水”,说完,换了雨靴,操起一个手电筒和一件雨批,急匆匆出了门。
屋外,俨然成了一个混沌初开的风雨世界,黝黑的夜如鬼魅一般,吞噬所有可见的一丝光亮。水生三步一趔趄,在泥泞不堪的村路摸爬行进,瓢泼大雨倾泻在脸上,如针灸般刺痛,终于来到了大坝,水生持手电照去,闸门兀自关闭,想必是停电之后控制开关出现故障。大坝南侧的龙门浦水,已完全成了脱缰的野马,以势若奔雷、力贯千钧之势涌向上游的村庄,如不及时打开闸门,不仅大坝溃于一旦,上游的数千亩农田村舍也将悉数成为汪洋泽国。水生来不及遐想,电光石火绾起袖子,钻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机房,用手扳动闸门罗盘,随着铰链发出清脆的咬合声响,带动罗盘飞速旋转,大闸终于被打开了!狂风,伴随着久已蓄积的洪水,如泰山压顶一般扑来,将徒手的水生裹挟进了这淘淘奔流中……地上,微弱的手电光尚在斜雨疾风中飘乎不定,夜幕后,传来初春撕心裂肺的叫喊。这喊声,会让水生熟悉到笃定,让黑夜变得透亮,让浊浪变得轻盈;这喊声,似从二十年前的河岸飘来,穿过黝黑的夜,跨越时光轮回,替所有驻足守望之梦以绿油油的希望。
三
龙门浦,又不竭奔涌三十年。
四季轮回更替,龙门浦已拓宽成五十米的大河,河水依旧,只是岸上等候的女子已两鬓成霜。
河岸两侧宽阔的现代公路,车流不舍昼夜。一望无际的菜花田只遗留一脉子嗣,每到春水初漾,太阳色的花骨朵总能在田间探出脑来,凝目注视百年一遇的防洪大堤,在阳光下巍巍耸立。
大堤旁的河岸,红旗依旧招展,窗明几净的新修教室,传出阵阵琅琅书声,一名年近花甲的清癯女子正带头引导孩子们诵读《老子》,“水,利万物而不争”。诵及此处,眼角隐隐泛出几滴泪花,与波光粼粼的龙门浦水一样,在阳光下散发珠玑的光芒。
被风吹开的讲坛课本,斑斑驳驳,发黄的扉页,赫然留有一行娟秀的文字:
春水初生,春林初盛,春风十里,藏着你。